基于精英决策的社区矫正司法制度分析
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历经10年发展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它作为中国刑罚执行方式的创新实践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究其根本,是我们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偏差,对这种偏差的修正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区矫正在中国社会的健康成长。
本文拟以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社区矫正为例,运用精英决策模型以社区矫正刑事司法制度在基层的生长状态、现实困境和完善路径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刑相对应的非监禁刑事司法制度,本文拟从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社区矫正实践的视角,运用精英决策模型对社区矫正刑事司法制度在基层的生长状态、现实困境和完善路径谈点个人的想法。
一、问题由来
社区矫正在中国虽已经过了十多年的试点和发展,但是,相关的理论研究尚不成熟,实践经验还需积累,各种问题亟待解决,2012年出台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意在继续探索社区矫正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建设路径,这本是一个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笔者认为,不论是基于政治上功利主义的考虑,抑或是基于国情的科学抉择,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精英认识到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创新的框架下,完善和发展社区矫正制度是填补社会管控制度空白,确保社会安宁有序,完善人权司法保护制度的必然选择,必须正视社区矫正在刑事司法制度体系中的应然地位。
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我们正在犯的错误却也非常明显,特别是诸如政策目标偏差、政策环境阻碍、工作主体错位等根本性问题日益凸显,倘若不能及时认识和纠正这一系列问题,将严重影响和制约中国社区矫正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甚至会背离精英治理下社区矫正制度本来应有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二、理论框架
精英决策是指政策的制定过程,做出决策的主体是掌握权力的少数人。[1]精英决策模型是将公共政策看成是反映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们的价值偏好的一种决策理论,其基本内容是强调精英统治的必然性和合法性。这一模型是由托马斯·戴伊和哈蒙·齐格勒于1975年在《民主的讽刺》中提出,其基本假设和结论是:公共政策的形式和内容不是由人民大众通过他们的需求与行动来决定的,而是占统治地位的少数精英们最终决定的,然后由政府机构和官员去加以实施。[2]在中国,我国的政体也是代议制共和政体,代议制本身就决定了政府组成人员是人民委托的少数精英,其决策模式往往是精英模式。[3]我国精英决策的本质特征是在政治精英主导的政治过程中,一项决策的做出首先源于高层政治精英对现实的把握和推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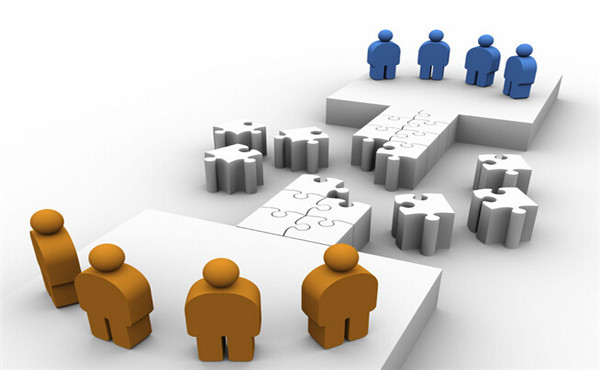
例如,在国家层面做出“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决策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中国的精英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的声音,但大部分人还不具备直接参与决策的知识和能力。基于以上理论,精英决策模式下社区矫正替代监禁刑,减低监禁率,降低刑罚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价值和意义如何体现,取决于政治精英是否能够尊重科学的精神和原则。
三、分析与论证
(1)政策目标分析。实践中,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是“硬指标”,大量工作围绕加强管控展开,通过提高见面率、限制外出等措施,以减少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概率。然而,刑罚对于预防和减少犯罪的效果都是极其有限的,同样是对罪犯的惩罚,监禁刑的惩罚过程应当更加漫长、艰难甚至痛苦,监禁刑的“矫正”措施和效果与非监禁刑的“矫正”相比是全方位的,然而,监禁刑罪犯在刑满释放后的重犯率却远远高于一般公民的犯罪率。[4]监禁刑尚且如此何况社区矫正?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是监狱还是社区矫正机构,他们真正有能力管控的仅仅是罪犯在服刑期间的重犯问题,一旦刑满释放或者解除矫正以后,重犯与否则不再作为关注的考核指标,而这恰恰是非常可悲的。随着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假释、缓刑、管制、监外执行等适用的不断扩大,以及其他适合社区矫正措施的轻罪处罚法律规定的产生。
例如,大量的因“酒驾入刑”获刑的人员。决策者希望看到的是社区矫正的迅速成长,使非监禁刑的社区矫正与监禁刑的监狱矫正成为刑罚执行的两种并驾齐驱的执行方式,实现刑事司法领域的历史性突破。因此,监禁刑核心在于矫正,非监禁刑核心应在社区,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所在。
(2)政策环境分析。在中国,传统的农村集体共同体社会不断解体,新的城市社区共同体尚未形成,“社区”作为社区矫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层社会基础显得非常弱小,介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社会第三方力量”非常匮乏。以华漕镇为例,辖区29个村、居委并存,实行以镇党委、政府为领导核心、社区组织为补充的“镇管社区”模式,“社区”基本等同于行政区划。实施社区矫正的正式主体是司法所,社会工作者、村居委干部、罪犯的亲属、朋友等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看似社区矫正工作已经走上了“政府主导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的良性发展通道,事实上,“第三方力量”的参与度和作用发挥却非常有限,更多的是根据官方的“具体要求”配合做好对罪犯的管理服务工作。真正意义的社区矫正的主体应当是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工作者,社区矫正中的政府应当从“全能政府”转为“有限政府”,以购买社区矫正服务的方式提供财政保障,以组织者、指导者、评估者的身份进行组织、协调、指导,在社区矫正工作的各个环节引入社会组织为服刑人员提供服务和帮助,使他们逐渐养成正常人的行为习惯复归社会,这样,真正意义的社区矫正才得以实施。[5]
(3)政策运作分析。近年来,全国社区服刑人员数量一直处于高位并不断攀升,据统计,截至2014年6月,全国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99.4万人,累计解除127.2万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72.2万人,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再犯罪率为0.17%。
[6]社区矫正机关的人、财、物等保障水平与日益繁重的教育改造任务和日益增大的监管安全压力而言仍然比较薄弱。司法所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人员基本上是“1名公务员+若干名社工”,社工按照社区服刑人员总数“30︰1”的比例配备;按照现行政策,执法装备和交通工具的配备,独立用于宣告、教育、劳动的场所难以落实;经费保障标准亦无统一标准。
另一方面,近年来社区服刑人员总量直线上升,以华漕镇为例,2013年开始,在册服刑人员由年初的不到50人达到了年底的近90人。沪籍与非沪籍人数严重倒挂,2014年接收的123名社区服刑人员中,沪籍仅38名,非沪籍达85名。在中央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上海市各人口导入区县正在大规模实行人口调控政策的大环境下,应当提高保障水平,合理设置纳管准入门槛,科学配置有限的社区矫正公共服务资源。四、对策与建议
精英决策模式下的社区矫正刑事司法制度在基层的运作与决策者的想法还有很多出入,因为观念的、体制的和结构的等等根深蒂固的原因,已经造成了政策执行中的各种偏差,社区矫正政策决策系统亟需改进。
一是观念和理论的更新。刑罚之惩罚性是第一位的,社区矫正的惩罚性是必然的,但是在当前国家层面精英阶层的主流思想由社会管控向社会治理转化的大背景下,我们非常有必要认清非监禁刑的社区矫正与监禁刑的本质区别,社区矫正应当着力于罪犯行为的养成,现在很多地方所谓的“收得下、管得住、跑不了”的“成功经验”根本不是社区矫正所应当追求的目的,过度地强调管理和控制反而扭曲了社区矫正的本来意义,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要尽力避免社区矫正制度因为错误的观念和理论而背离科学的发展方向。
二是摒弃部门利益之争。虽然说在目前大规模适用社区矫正的情况下,各地确实有困难,开展工作所需的人员力量、执法装备、保障经费等最基本的条件尚未得到进一步的解决,然而,任何借发展社区矫正事业之名的权力博弈都将严重阻碍社区矫正在中国的健康发展。例如,在执法主体资格没有任何合法性依据的情况下抽调戒毒警力到区县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变社区矫正为警察矫正、警察行刑。再如,将监狱的管理模式平移到社区,构建没有高墙电网的社区监狱,既没有实质意义,更是历史的倒退。
三是适度扩大民主参与。社区矫正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的发展,必须综合考虑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不能将社区矫正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人为地割裂开来,在社区矫正基本内容的探索和设计过程中,应当有意识地扩大民主参与度,允许基层执法部门、基层自治组织以及公众等等参与社区矫正的发展,听取基层的声音,关注基层对社区矫正的判定,纠正不恰当的做法,注重社区建设、培育社会组织、发展社会工作者,为社区矫正步入健康持续科学发展之路排除阻力、创造条件。
作者:张峥华 来源:经营者 2014年12期
上一篇:浅析我国青少年司法制度
下一篇: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完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