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刑法中数额的规定
我国刑法的罪名约有400余种,其中约有300余种对犯罪数额有要求。这些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或由刑法直接规定,或由司法解释界定,不但影响着量刑的轻重,有的甚至直接决定着犯罪的成立与否,是某些犯罪的必备要件。因此,确定犯罪数额标准对于准确适用刑法具有重大影响。在我国当前刑事法律体系结构下,数额成为某些行为是入罪还是出罪、罪重还是罪轻的标杆。根据刑法分则中数额的规定方式是具体还是概括为标准可以分成确定性数额和概括性数额。
概括性数额是指刑法上对数作了概括性的规定,在司法认定时需要先将概括性的数具体化后才能适用。这由刑法调整对象的复杂性所决定。法律对于社会关系调整不是随机、个别的调整,而是一般的调整。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变易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与大小也会发生变化。因此,不采取精确的描述,而使用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概念,能够使刑法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例如刑法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盗窃罪。通过概括性的语言“数额较大”对构成盗窃罪的数额标准进行限定,但“较大”法律并没有明确。
确定性数额是指在刑法上规定了具体的数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在司法认定时只需直接将案件涉及到的数值、数量直接对照法律规定即可。如贪污罪,明确规定了具体犯罪成立的数额标准:“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我国1979刑法中没有规定确定性数额;现行刑法中加入了少量确定性数额的规定,但概括性数额仍占绝对优势。这是因为:一是立法技术的要求。法律是以极少的条文,来调整复杂的社会生活,故条文力求其少,文字力求其短。二是防止刑法的不适应性。我国正处于经济大发展时期,立法者如将数额都进行具体化处理,很难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概括性数额具有“质”的稳定性。这就决定了概括性数额具有适应性,从而保证了在不同时间段内实质公平。但概括性数额具有以下问题:
其一,有权具体化的制定主体多,甚至有些标准长期不出台。概括性数额具体确定的主体也显得比较混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甚至行政机关都在参与这个过程,另外一些犯罪到目前为止,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联合制定了立案追诉标准规定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却没有制定数额巨大的标准。
其二,难以实现罪刑均衡。概括性数额的具体内容总是处于变化中,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案件,其数额与社会危害程度上就难以保证对应。比如,在江苏省盗窃五万元在2012年评价为“数额巨大”;但在2013年则评价为“数额较大”。特别是在概括性数额转变成具体性数额的过程当中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进一步导致具体化后的数额不能与其社会危害性程度相匹配。
其三,不利于保障人权。概括性数额的模糊性导致了普通民众难以分清犯罪和违法的界限,从而无法预测自己的行为所受到的刑法评价,而人权的保障、行动的自由,恰恰有赖于公民对自己行为的预测可能性。公民如能预测自己的行为性质和后果,就不会因为不知道行为的性质而侵犯他人的利益;同样,公民如能预测他人的行为,就不会总是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而感到不安。
因此,在1997年刑法中就加入了少量的确定性数额。确定性数额符合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有利于限制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发挥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但确定性数额的缺陷同样明显,主要表现在:其一,具有滞后性,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确定性数额是立法者根据立法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确定的,该数额代表的是立法时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发展是当前的主题。立法时设定的数额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程度难以适应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其二,难以适应我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刑法中的数额一经确定后将适用于全国各个地区。但是很明显,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因此同样的币额在不同区域所代表的实际价值,有时差距很大,其所代表的社会危害性的量也是不一样的。以统一的数额标准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犯罪的方式有失公平。其三,从技术上看,刑法规定越具体就越僵化,漏洞就越多,容易形成空当,妨碍了刑法保护功能的发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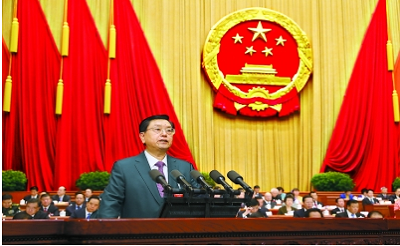
罪刑法定主义原则是以立法权限制司法权,以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不受司法侵犯。但是刑事司法并不能当然地实现罪刑法定主义,其相对于刑事立法来讲有其相对独立性,既可能实现罪刑法定原则,达到保障人权、保护社会的目标;也可能破坏罪刑法定原则,使符合罪刑法定主义的立法也成为空文。而要在刑事司法中达到目标,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司法自由裁量权与罪刑法定主义的关系。
确定性数额加强了立法权对司法权的限制,使得适用刑法时变得简单。司法机关只要将行为及其数额与刑法所规定做一个机械的对比之后,便可以确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及其法定刑幅度。但是,确定性数额是在立法就已经被固定了的,并将在相当一段时间被保持稳定。除非修改刑法,否则不能通过其他方式随意改变。因此大量绝对确定性数额规定在刑事法律中出现是不适宜的。然而,在司法中概括性数额规定也存在着存在很大的缺陷:
第一,概括性数额的模糊性在刑事司法中必须明确化。司法机关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数额,这些数额必须与刑法规定相比对,才能确定行为的性质,区分究竟是一般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并进而确定其法定刑幅度。而这种比对的前提就是需要将概括性数额进一步明确化。
第二,立法中概括性数额的规定方式给了司法机关发挥其自由裁量权的巨大空间。司法机关需要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才能更好的达到罪刑法定主义的目的。如果自由裁量权并不充分,司法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得到发挥,则难以实现将罪刑法定化的死法转变为活法的法律效果,但自由裁量权的空间过大,则易陷入罪刑擅断主义,从而颠覆罪刑法定原则。
要弥补概括性数额的两大缺陷,关键在于将概括性数额明确化的方式是否合理,而不在于规定方式的本身。只要处理好了这个问题,概括性数额是完全能适应刑事司法的需要的。概括性数额具体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经途径。概括性数额具体化实际上是关乎我国刑法中的数额的规定能否具体付诸实施的问题。目前,都是采取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的。这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可以选择:
第一条途径是参照我国刑法上规定,将所有的概括性数额规定修改为绝对确定的数额规定,也就是说将各种“较大”、“巨大”等具体规定为固定的数目标准(或幅度),这也是目前的方法。司法机关不仅要对以往的各种经济犯罪或者财产犯罪进行调查,掌握大量的实际数据,还必须根据财产、经济犯罪受社会经济发展变动影响最大的特点,对司法解释颁布后一定时期内这些犯罪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出预测。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大发展时期,这也无疑大大加大了司法机关实现这一途径的难度。况且,采用绝对确定的数额规定方式,其缺陷已经很明显的。
另一条可能的途径就是参照俄罗斯的规定,以相对数将概括性数额进一步明确为相对封闭的数额。《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对“经济活动领域的犯罪”规定的等都采取了规定相对数额的方式,而且在构成要件上大多数使用的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相当巨大”规定,这与中国刑法上的概括性数额规定是一样的。但是,俄罗斯对概括性数额均做了解释性规定,是按照“最低劳动报酬”为标准,根据“最低劳动报酬”的倍数来确定“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有些是200倍、有些是500倍。由于法律规定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计算标准,所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具体内容是相对固定的,而由于 “最低劳动报酬”是随、经济发展而变化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数额也是过一段时间就发生变化。这样的好处在于维持了刑法的稳定性的同时又避免了刑法的僵化,解决了刑法的稳定性与社会适应性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俄罗斯的规定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确定基数。基数必须兼具确定性和变动性的特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指标。这个基数也因我国每年都公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具有浮动性。根据我国现状,可以分为两类分别采用不同的标准。对普通刑事案件的犯罪,因为不同地区的人对财产的多少的感觉差异较大,较多的体现地区差异,可以采用省一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基数;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因为公共财产属于国家,国家的发展水平体现了公有财产的价值,宜采用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基数。
第二,确定倍数。也就是要确定各个具体数额究竟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少倍或者比例,以建立概括性数额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固定的对应关系模式。可以采取固定的倍数或者比例,供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在定罪量刑时具体处理。
总之,我国概括性数额具体化的目标定位,笔者认为在刑事立法中,既要以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为目标,又要注意发挥刑法规范模糊性的积极功能,二者的协调与平衡是刑事立法的目标所在。
作者:卢兴龙 来源:法学教育 2014年5期
下一篇:刑法立法和司法解释应注重条文协调
